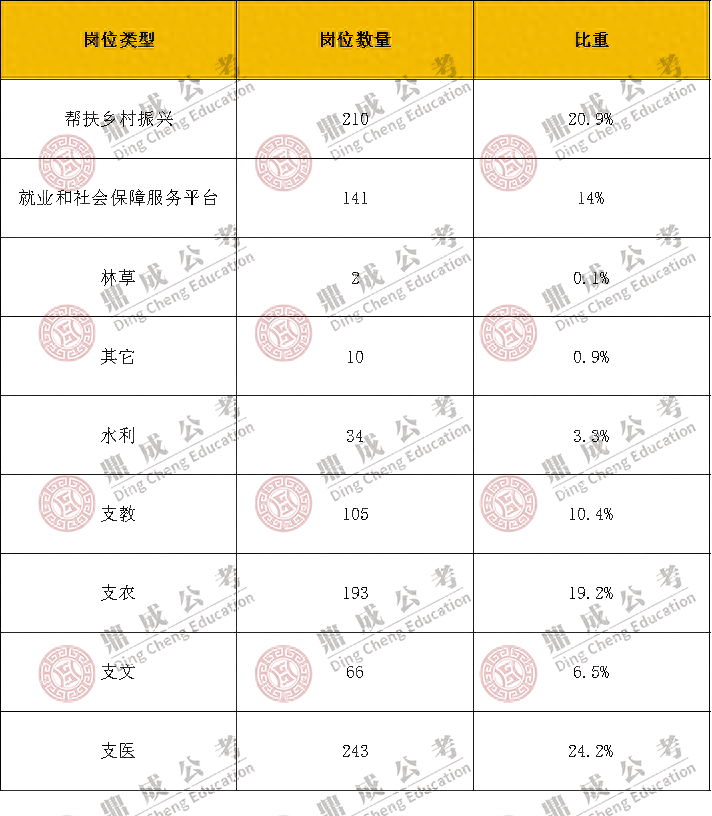“越辩论,真理越明晰”。在法律界,由于不同学者之间理念的差异,以及法律思维逻辑的多样性,分歧与争议在所难免,从而导致法律问题上存在一些极具争议的灰色地带。正如经典的《洞穴探险者案》给我们展示的“十四位法官,十四种意见”,我国著名的法律学者也对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意见碰撞。学术的争论是法学理论不断进步和发展的一种表现,在这些讨论中,法律学者的观点针锋相对,各执一词。让我们回顾几场著名法律学者之间的经典辩论,感受法律思维的奥秘。
来源:明德律师事务所、广西法律学院
刘勇再审纠纷案
争论焦点:法律学者是否有资格发表意见?
支持者
周光全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肖晗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反对者
易延友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何兵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陈杰荣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
2002年,刘勇涉黑团伙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该案一审被铁岭中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二审时辽宁高院却将其改判为死缓,引起社会轩然大波。
据悉,该案辩护律师田文昌组织陈光忠、陈兴良等14位北京国内知名刑事法律专家进行论证,形成了对刘勇有利的《专家论证意见》,并提交给二审法院。该意见认为,一审判决存在问题。此举引发学者们的热烈讨论:专家有资格向法院出具法律意见吗?这样的意见会不会干扰司法审判的独立性?
何兵教授首先发表了《律师,你有什么资格向法院出具鉴定意见?》一文,严厉批评法律专家的做法,认为这是对司法独立的公然干涉,是不当行为。在他眼中,法律专家意见是“对法院施展的无形神掌”。
肖寒教授在《也谈司法过程中的法律专家意见》一文中对此进行了含蓄的批评,他说,国外有“法庭之友”制度,法院可以邀请专家向法庭表达意见,为什么我们的法律专家就不能向法庭提交法律意见呢?
随后,易彦友教授以《对法学专家发表的专家意见的质疑》一文参与讨论,认为本案的专家意见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专家应辩论的范围。
几天后,周光全教授在《专家意见的实践合理性》一文中表达了支持,并阐述了对“中国式”司法实践的看法。
陈杰荣教授撰写了《刘永案,中国法学界的耻辱还是荣耀?》一文,明确表达了反对态度。
刘永案的大辩论,让我们深刻体会到学人维护司法公正正义的奉献精神,以及法学人对法律人自我定位的反思。
民法典编纂中的梁、王之争
争论焦点:人身权利应否独立为一章?
支持者
王黎明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杨立新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反对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梁惠星
孙宪忠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教授
民法典编纂五年来,学界对中国民法典的立法模式、立法技术等问题有过许多不同看法,争论不休。其中,关于人格权是否应单独编纂的争论尤为激烈。双方代表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两位学术大师。支持者是全国人大王利明教授,反对者则是民法界的领军人物梁慧星。
自2000年初以来,双方均发表文章讨论民法典编纂问题。梁慧星教授曾数篇文章从双重适用原则、自卫权、居住权、无权处分问题等角度阐述人格权为何不应单独编纂,甚至建议暂停民法典编纂。其间,《民法典编纂中的重大争议——法制工作委员会对人格权法典两稿的评论》《民法典颁布前,再次郑重建议删除人格权法典》等文章相继发表,让读者深切感受到一位有良知学者的学术坚持和历史担当,感受到一位年逾古稀老人的嘶哑语气和恳切语气。
另一方面,王黎明、杨立新两位教授在法案起草时始终坚持立法观点,认为这是民法典的最大亮点,不能因为有争议就抛弃人格权独立划分。王黎明的发言和文章《乌克兰民法典与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有何关系?》、《民法典编纂中的几个争议问题——对梁慧星教授几种意见的几点回应》认真阐述了人格权独立划分对于保护人民人格尊严的重大意义。
2017年,全国各地民法学者和实务界对《个人权利法典》的讨论愈演愈烈。在正反两方的声音中,除了梁、王二人之外,不少民法学者持中立态度。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开祥表示,多数人认为“独立也可以,不独立也可以,纯粹是立法制度安排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法学学者江平的发言几乎起到了压轴的作用,他对此次争论的主要问题做出了定论,认为人格权法独立编纂是最可行的途径。江平教授关于人格权的深刻立法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至此,关于人格权法是否应独立编纂的“两王之争”暂时告一段落。
张扣扣案争议
争论焦点:张扣扣应否判处死刑?
支持者
北京大学法学院学位委员会主任 朱苏利
谢望元 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学教授
王正勋 西北政法大学教授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佟志伟
反对者
周永坤 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冯军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扣扣辩护律师邓学平
2019年,一篇题为《一叶一沙,一个世界》的辩护词在网络上疯传,不仅引起法律界的关注,也引发了全国范围的热烈讨论。这是邓学平律师在张扣扣案一审中发表的辩护词,舆论中出现了一褒一贬的两种观点。对于学者来说,张扣扣案的争议早已超出了案件本身,纠缠在“同质报复”、死刑、死刑复核、辩护的价值,甚至公权和法律本身的价值等极其重要的话题上。可以说,此案是第一起引发网络法律意见领袖大辩论的案件。
为了报仇,张扣扣残忍地杀死了三个伤害过他母亲的人。赞扬者称他的辩护“史诗般”“教科书式”,批评者则认为其辩护过于煽情,缺乏说理。在法学界的大讨论中,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在支持死刑的人群中,北京大学教授朱苏利第一个撰文表示支持法院判处张扣扣死刑,并称律师的辩护极其偏颇,“一堆纯属空洞的民学(社会)学借口”,刻意无视案件的基本事实,并提出严厉批评。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谢望元也认为,张扣扣采取的“私力救济”方式不能超出法律的范围。
西安政法学院王正勋教授从张扣扣案的法律和人性角度探讨了报复的合法性以及私力救济的局限性。
华政大学教授佟志伟表示,一条命换一条命,对张扣扣不应从轻量刑。但他同时表示,邓律师的辩护“是基于事实和法律的良好刑事辩护产品”,并认为苏文的态度和表述有些不恰当,甚至带有霸凌的意味。
反对死刑的“辩手”们也提出了不少精彩观点。苏州大学教授周永坤认为,张扣扣的行为“事出有因”,批评苏莉的文章对律师辩护进行莫须有的指责,评论多处“令人心酸”,呼吁尊重律师。
人民大学冯军教授表示:“张扣扣确实不该这么早就死。朱苏利教授的供述既不真实,又不合法,完全是错误的。”这份辩护书真是一篇高明之作。
辩护律师邓学平本人对上述讨论作出了回应,认为法律工作者不应该把自己局限在某个领域或者给自己设限,文学不是法律的敌人,本辩护词大部分内容是法律分析。
引人深思的张扣扣案随着时间的流逝落下帷幕,但这场争论带给人们的思考却永远是新的,法律界也在这样的不断批判与反思中成长、进步。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争论
争论焦点:刑事责任年龄应否降低?
支持者
肖胜芳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
罗翔 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
反对者
宋英辉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吴宗宪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王牧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顾永忠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近年来,未成年人杀人、重伤他人案件频频见诸报端,不断进入公众视野,一再刺激公众脆弱的神经,引发人们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担忧。2019年,大连一名十岁女孩被十三岁男孩蔡某杀害,因行为人未满十四周岁,依法不负刑事责任,引发社会热议。在此背景下,现行刑法是否有必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成为刑法界不断争论的焦点。
“降低说”者认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可以发挥刑法的震慑作用,防止未成年人犯罪,是遏制未成年人犯罪的现实需要。
中国政法大学刑法研究所所长罗翔教授认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势在必行。对于犯下滔天罪行的未成年人,即使能够教育矫正,也要在刑罚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在条件成熟时,可以将刑事责任年龄降低至十二岁。
江西省律协副会长冯帆表示,从心理和生理年龄上看,如果对未满14周岁的儿童不承担责任,可能不符合儿童目前成长条件。应在现行刑法年龄基础上适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避免对未满14周岁的青少年实施暴力犯罪“放任不管”。
对此问题持“不变”观点的学者也不乏其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宋英辉撰文指出,应理性看待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科学性、专业性的判断不应受极端案例或社会舆论的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吴宗宪在演讲中表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不良后果是,会扩大犯罪圈子,可能增加监狱的运行压力,增加社会稳定的压力,严重损害国家文明进步的形象。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牧表示,犯罪低龄化是世界趋势,但不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是对犯罪问题理性认识的结果。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顾永忠建议,应该将刑事责任范围由14周岁扩大到16岁以下,即对一些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予以刑事追责的问题,不应轻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刑法学界和实务界对是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主要观点是降低说和不变说,此外,也有折衷的观点。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婉华、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戴秋英等人表示,是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需要多维度考察,针对不同类型的犯罪行为可以采取不同的刑事责任年龄。他们呼吁多措并举解决未成年人不良行为问题。
收买被拐妇女刑事责任之争
争论焦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应否提高?
支持者
罗翔 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
王锡新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反对者
车浩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白浪涛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徐州凤县一女子被关押后生下八个孩子的新闻,引发了舆论风暴。法学界对收买拐卖妇女儿童罪的量刑配置展开了热烈讨论,不同观点的碰撞十分激烈。争论的双方各执一词:以车浩、白浪涛教授为代表的“维持派”主张维持现状;以罗翔、桑本乾、王锡新、李敏教授为代表的“改良派”主张加大量刑。
此次学术讨论“破圈”并引发社会关注,由此引发的舆论和压力很可能对未来的制度设计产生影响。双方的实质性争议主要有两点:如何用刑罚精准界定和表达拐卖妇女的罪恶?修法增加刑期是否有助于遏制和解决拐卖妇女的罪恶?前者可以简单称为立法层面的“恶之度量”问题,后者则是执法层面的“恶之矫正”问题。关于立法层面的“恶之度量”问题,分歧在于如何确定犯罪程度,具体比较方法有两种。
一是“以人比物”。“改良派”罗翔教授批评收买被拐妇女最高刑期只有三年,称“人不如物”。王锡新教授也指出,此类案件的核心是违背了社会共同体的核心价值,即每个人都有不受统治和奴役的权利。基于对这一核心价值的保护,对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罪的量刑应当加重。“维护派”车浩教授反驳:两种罪名看似都在惩罚收买行为,但收买的含义不同。罗翔教授进一步反驳:虽然从罪名数量上看,对人的保护力度更强,但在基本量刑上,单纯的收买妇女儿童罪与收买珍稀野生动物罪仍然存在严重的不平衡。 对此,白浪涛教授指出:由于人与动物所保护的法益性质不同,买卖动物与买卖妇女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另一类是“人与人之间比较”。罗翔教授呼吁“买卖同罚”,依据是,根据同犯量刑基本相同的法理,非法买卖枪支罪,买卖双方都受到同等处罚,购买假币罪与贩卖假币罪也受到同等处罚。而拐卖妇女儿童罪与收买妇女儿童罪的量刑差别很大,这在法理上是不能接受的。车浩教授则主张,不应同等处罚,依据是买主的罪恶程度小于贩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