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月她妈
应该保持什么关系——专业关系抑或是朋友关系? 案例:服务对象外出旅游,从外地带回礼品,特地来到社工点送给社工,还一再强调,是他的一片心意,不收下就是看不起他。作为社工的我是否该手下礼品呢?如果收,是否要还礼呢?如果不收,我该如何拒绝服务对象呢? 就这个问题我认为是表面上看似复杂其实可以简单化的。只要 理清 脉络,界定好关系即可。我们要设身处地的将自己放在真实情境中去考虑问题,我们需要考虑多种因素的影响和明确行为的双向互动, 理清 影响行为后果的因素到底有哪些。 第一是考虑所处的服务阶段,如接案阶段、建立关系阶段、评估阶段抑或是结案阶段等。 1.接案阶段:社会工作讲究实证主义,倡导人在情境中,我们可以设身处地的假想一下,在接案阶段案主有没有可能会给社工送礼品,从现实出发我们会给一个不熟悉的人送礼品吗?,当然不会,况且社工机构或社工不同于行政部门或行政人员即便是社工还没有做什么工作去帮助人家或打动人家,案主又怎么会送礼品给社工呢? 2.建立关系阶段:在建立关系阶段处在社会工作服务的关键期,是社会工作者同案主关系极不稳定的时期,案主即便是给社工送一些礼品更多的也是试探性或礼让性的表达,比如:初次探访案主家庭情况,案主请社工吃水果或给案主倒了一杯水,在中国我们不能轻易的界定为“伦理两难”,我们在讲求专业性的同时更要走下神坛,走进民间,如果你不接受案主的礼让那会显得案主招待不周,或你不懂礼貌,社会工作就是入乡随俗,随机应变,即便是西方的社会工作来到中国的山头也要唱中国的歌。同样我们到西方国家去也要用媳妇那个人呢的思维同当地人交流,否则一切谈话都是徒劳。所以此时的社工完全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一般来讲案主都不会太强求,如果非要接受可以向案主说明机构的要求和纪律,总之在这个阶段是可以平稳地度过所谓的“伦理两难”。 3.评估阶段以及接案阶段:在此阶段,甚至以后,社会工作者同案主已经建立了牢固的专业关系,甚至是专业关系和朋友关系并存的双向活动关系,即在工作中的专业关系,在生活中的朋友关系,此时的社工完全能够理清同案主的界限,可以灵活处理这类伦理两难问题,案例中提到礼品仅代表案主个人的一片心意,所以此时双方是在私领域中的互动,也从侧面说明社工同案主的关系,以及社工的确给予了案主很大帮助,从功利角度来讲,是案主自身的回馈,从专业角度来讲,也算是实现了“助人自助”。 第二是考虑案主的经济条件。我们都知道一个连温饱问题、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的人如何去谈及发展与享受。案例中提到礼品是案主旅游时带回来的,既然能够外出旅游,说明案主的经济条件并不是太差,或是差到连饭都吃不起的地步,因为即便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农村,很多人也没有时间精力或经济条件去完成一次不大不小的旅游。另外,外出旅游带回来的小礼品大多应该是地方特产或纪念品,价格也不是太贵,更多的是纪念意义,也可以理解为象征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在专业关系稳固,多元化关系并行的阶段社工完全可以接受。不过社工在接受的同时一定要强调这种行为是在私领域中进行的,明确行为关系的界限。如果案主家庭条件特别优越,所馈赠的礼物十分贵重,那作为社工无论从哪个关系的角度考虑都不能随意接受,那如何做到既不接受贵重礼物的馈赠又不至于打击或伤害到案主呢?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是向案主讲明机构的规章守则,以及接案时签订的服务协议,再次提醒案主双方的正式关系,委婉拒绝; 二是如果案主执意馈赠贵重礼品,可以馈赠替代,即选择案主的小物件或其他物品作为礼物; 三是馈赠转移,劝说案主致力于公益事业,回报社会,救济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达到转移案主馈赠目标,实现委婉拒绝案主贵重馈赠。 还有一个问题是接受案主礼物后还要不要回赠礼物? 对于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是应该回赠的,社工帮助案主是责任所在,是出于道义,而案主馈赠社工礼物是在私领域,不能说社工帮助案主了就应该接受案主礼物,当然毫不客气的说,也不排除案主不送礼不安心的矛盾心理,在中国是很常见的,如到医院看病,不给医生送红包感觉不放心好像进了手术室就成为永远的诀别一样。在中国是人情社会,讲究礼尚往来,社工也应从私领域的个人角度回赠案主礼物,也以此来向案主阐明专业关系同朋友关系抑或是其他关系的界限。 我们都知道,社会工作是从西方引进来的舶来品,在我国不仅发展时间短暂而且经历曲折,中国的沃土有与众不同,中国是特色的、而又积淀传统的,需要境遇化和本土化,其中本土化并不影响发挥它的专业化,正如“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之所以“橘生淮北则为枳”是因为水土不服,气候、土壤的不适应,没有实现橘子的“本土化”,正如社会工作,即便是从西方引进到中国,在中国生根发芽,只要实现了本土化就不会影响到其专业化的发挥。我们总是讲人在情境中,我们思考问题也应该将问题放在现实的情境中去思考而不是放在理想的沙盘里去讨论,同样理论应在它所适应的范围内讲解,在超出它所适应的范围只能是探索或检验。西方的理论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来到中国“水土不服”也在情理之中,我们不能用南方栽种水稻的方法去北方种麦子,不过我们到可以从种水稻中汲取经验,移植到小麦种植中去。就好像用中国传统文化思维去解释发生在西方国家的事例不太合适一样。 我并不认为社会工作是很难发展的,相反我认为社会工作在中国尤其是在未来的中国发展前景是可观的,目前、我们对知识和理论展开深入的探究和思考也没有什么过错,只是有些问题我们没必要“钻牛角尖式”的纠结,就好像一群村口大树下的老太太边择着菜边拉着家长里短,每天都喋喋不休的争论仿佛也没有什么结果,日子还是照常过。有些问题甚至是没有必要不停地讨论下去的,有这些功夫和精力还不如多做些实事,像本土化和专业化两个概念看似简单,当然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但却总是听到有人无数次的在探讨着。对此我很是不解,我认为人不是机器,教科书也不是圣人言,即便是老师也不能做到不掺杂任何个人感情的做一件事,没必要在提供服务的时候非要精确到“飞秒”甚至更小。在社区打扫卫生,做一些看似无聊的活虽然简单,但生活不就如此吗,不是每个人非得干出惊天动地的伟业。在平凡的世界里能把最普通、最平凡的事做好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2019年3月19日星期二 写于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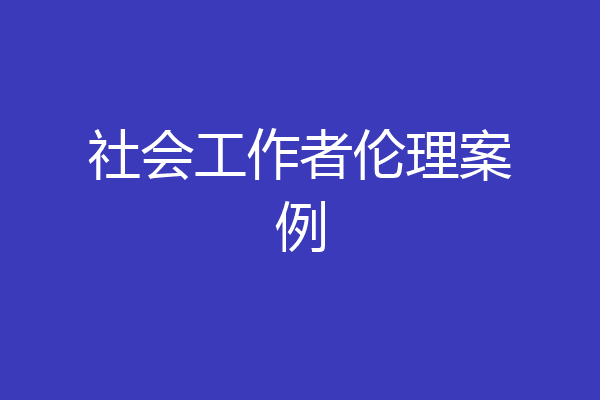

么么三姨
社会工作介入儿童虐待问题伦理困境
在中国的社会文化情境中,孩子和父母是怎么理解虐待儿童问题的?父母打孩子是不是儿童虐待?他们怎么解释暴力发生的原因以及对亲子关系的影响?那么,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介入儿童虐待问题伦理困境分析,欢迎大家参考阅读。
问题的提出及背景
2014 年4 月-8 月,笔者在广州市某中学做驻校社工服务,同时参与了一个关于儿童保护的项目,便在实习站点所在的学校开展了“防止儿童虐待小记者行动计划”小组。该小组通过观看国内关于儿童虐待的新闻报道、观看国内外宣传儿童保护的海报及公益片、扮演情景剧、外出采访社区居民、共同拍摄宣传公益片等形式,让青少年(初中生)结合自身的经验及一些新闻报道,表达对儿童虐待的看法,增强他们对任何有可能造成身体伤害的行为有分辨能力,提高他们对儿童虐待事件的敏感度及社会责任意识,并到社区里进行社区倡导。
在小组开展过程中,组员能够坦陈自己童年被“家暴”的经历、对经历回顾的感受和现在的看法,他们对小组的信任和坦诚让社工感受到了小组的力量。但笔者发现,有的组员遭受家庭暴力的严重程度远远超出了笔者的想象,而笔者在介入中也遇到了一些困境。
案主GXS 即是其中一个严重的被虐个案。她常在大热天穿着长袖衣服,社工怀疑她目前存在被虐待的危险,便邀请她参与小组。在小组活动中,GX S 曾四次因看到社工分享的图片、听到组员分享的信息而哭泣。GX S 袒露她从1 岁到上六年级一直受到父亲的暴力相待,母亲在她3 岁时因受不了父亲的家庭暴力而离婚。她也很想逃离父亲,曾在很多亲戚家居住。其父曾用皮鞋、皮带、木棍、铁水管、煤气罐威胁爆炸等方式对其打骂,父亲喝醉酒、不高兴、没钱都会拿她出气。她5 岁左右时,一天在房间里睡觉,父亲偷偷进来摸其性器官,她日后每每遇到这种情况都会狠狠地咬父亲的手臂。因为过去父亲的暴打很严重,致使她的手臂在夏天很容易发炎流脓,所以穿长袖以免被别人看见。
在小组的第四节活动中,社工翻到一个海报时,有组员表示,“受过虐待的孩子即使事件过去仍会记住受虐的经历,甚至像海报中的那个人一样自己去伤害自己”。这时GX S 大声喊:“对,就像我一样!”当时,G X S 一个人走到笔者身边,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小刀说:“M i s s,我跟他一样,经常拿这个割自己。”原来案主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想起那些受虐经历时,便时不时割伤自己。案主向社工展示,她的十个手指头都曾被自己割伤,都是小小的割痕,说这样很容易复原。
四个月里,社工与G X S 进行了六次面谈,发现老师对她过去的受虐经历和现在的自虐行为全然不知,其亲生母亲虽然知道却无法帮她离开父亲。社工作为改善案主发展环境和处理案主危机的主要干预者,在介入该案例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伦理困境,包括文化上的、法律上的、情理上的,笔者希望能够对这些困境进行分析和思考,以促进社会工作对儿童受虐案例的介入和思考。
社会工作介入儿童虐待问题的伦理困境分析
传统文化中父母与孩子对儿童虐待问题的建构
在中国的社会文化情境中,孩子和父母是怎么理解虐待儿童问题的?父母打孩子是不是儿童虐待?他们怎么解释暴力发生的原因以及对亲子关系的影响?
在小组进行过程中,社工引导组员分享自己曾经受到的严格管教方式或家庭暴力。组员T X 笑着说,爸妈曾经用衣架、扫把、棍子、皮带打她,她当时觉得爸妈很过分;F Y H 说母亲曾因他常常上网而让他跪下;L CH 说父亲曾让他在沙子地上跪了半个小时,膝盖都流血了。这些组员都认为,父母的这些体罚并不是虐待,自己当时的确做错了一些事情,父母是为了自己好。组员LZJ和案主GXS 则认为父亲对自己的暴力行为就是虐待,因为父亲经常把自己当成出气筒。而组员T X 的母亲认为,“父母打孩子只是为了管教孩子”,并反复强调自己是“为了孩子好”,是“气急了”才对孩子进行适当体罚的,她认为只有那些故意、恶意地打骂孩子的才是虐待。
我国传统文化对家庭暴力有一定的容忍和认同,不少人都认同甚至信奉“棍棒之下出孝子”“不打不成器”“打是亲、骂是爱”等观念,只有少数经常把儿童打得半死不活、遍体鳞伤的人才会受到指责,人们往往对那些由于目的和动机的善而实施虐待行为的人报以宽容和谅解,而很多孩子往往也认同父母是“为了孩子好”。因此,社工在面对儿童虐待问题时,要改变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非常困难。同时,当孩子面对被虐问题时,若社工告诉孩子说“你的父母正在伤害你”,是否会强化孩子对父母的敌对情绪呢?在这样的问题上介入,实质上社工要面对很大的挑战。
精神虐待难以评估与介入
长期以来,很多人习惯于把儿童虐待单纯地理解为对儿童身体上的伤害,对精神伤害则处于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状态。由于这种认知上的片面性,一些家长经常采取冷落、拒绝、孤立、恐吓的方式对待孩子,自觉不自觉地实施了精神虐待。
组员X LY 在小组中说自己小时候经常在吃饭时被爸妈赶出家门,这个自我披露得到了组员的共鸣,纷纷说自己也曾被父母赶出家门,不给饭吃。多位组员都表示自己曾被父母羞辱过,让他们感到自己笨、坏、毫无价值;被家人威胁丢掉或赶出家门;目睹父母吵架或有暴力行为。作为独生子女的T X 和L S X则表示被奶奶一直冷落,并被指责“你为什么不是一个男孩”。以上种种虽然没有给孩子带来身体上的伤害,但给孩子造成了心理上的创伤,以致某些组员看到一些相关图片或视频会流泪。
社工感受到组员的苦恼与沮丧,但孩子所受的精神上的伤害难以评定其持续时间的长短、是否具有经常性和反复性、次数是否频繁、后果是否严重等,在没有把握充分信息的情况下,很多精神上的伤害不了了之。但社工的伦理价值和道德责任感要求社工需在改变亲子关系上做出努力。为此,社工尝试与组员的父母取得联系,询问可否进行家访聊聊亲子关系,但大都遭到家长甚至组员的拒绝。一位家长甚至指责女儿不应参与社工站的活动,并以“学习为重”为由不让女儿继续参与,这让社工感到很无助。
专业伦理与法律法规的两难冲突
社工基于“保护生命”“最少伤害”的专业伦理原则,要确保案主不再处于受虐的危险处境,保护案主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减少案主的心理创伤。但我国的法律体系目前尚不够健全,现有法律对儿童的保护远远不够。此外,社工没有合法的权利介入儿童虐待案件,介入时要冒一定风险,介入后极有可能使施虐者得不到惩罚,反而变本加厉。法律没有规定可剥夺虐待父母的监护权,也没有机构可以收留受虐儿童,受虐儿童无法离开原来的生活环境,虐待消除的可能性非常小。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社工想为案主提供更安全的环境也是非常困难的。
专业界限与双重、多重关系
GX S 向笔者坦陈,她是因为当笔者是好朋友才将自己过去的经历告诉笔者的,她从来没跟别人说过这些事情,并强调若社工跟任何人说她的事情,便不再当社工是朋友。但社工初次接触这样严重的受虐并有自虐行为的案例,自身没有相关的实务经验,需要跟督导、导师探讨,这必然会泄露案主的某些信息,违背对案主“保密”的承诺。
此外,案主对社工的倾诉是基于把社工认定为私人的朋友关系,甚至曾让社工请她喝饮料或买零食吃。“当社会工作者和案主产生超过一种以上的关系,不论是专业的、社交的或商业的关系,即是双重或多重关系。双重或多重关系可能同时存在或接连发生。”由此可以看出,社工与案主之间的关系是单一的有限关系,一旦出现朋友、伙伴关系甚至性关系等,双重关系便形成。而对于我国社会工作而言,完全禁止双重关系的产生是不现实的。在中国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中,没有与案主建立亲密的“朋友”关系是难以让案主信任社工的。但若放任这样的关系形成,则有可能在进一步的服务中产生伦理困境。在介入儿童虐待这样隐私的问题时,双重关系更容易产生,这是否会使专业边界模糊,导致社工的专业角色混乱,或者过分关注案主,或者忽略了案主的实际需要。这样的双重关系无论对案主还是社工都会造成困扰。
结 语
儿童生存和发展不仅是父母的责任,也是国家的责任,国家有责任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提供服务等防止儿童的权利受到侵害,法律制度的完善、儿童保护机制的建立也能有效地支持社工承担自己的职责任务,减少在法律制度等伦理困境上的徘徊与挣扎,为儿童争取最大的权益。
同时,由于家庭是个私人领域,即使是专业社工,不经父母同意也难以介入家庭和接触需要帮助的孩子。同时,由于亲子之间特殊的感情和权力关系,儿童很少主动向外人求助。因此,对于较常见的父母打孩子的情况,社工的介入首先应该是帮助父母,通过父母对儿童的态度和行为的改变去帮助儿童,仅仅给儿童“充权”收效不大。
伦理困境是贯穿社会工作过程始终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是每一个社工面临的最严峻考验。社会工作在介入儿童虐待问题时要明确自身的责任和原则:一是确保儿童在家庭中不受到伤害, 二是确保父母在家庭中的责任和权利不受到损害。因此,社工应思考:在尽量不破坏家庭的前提下, 如何设计一个合法介入私人家庭领域的权利以保护儿童。
优质社会工作者证问答知识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