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小样丶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址位于上海市多伦路201弄2号(原窦乐安路233号)。“左联”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中国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团体。 2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为培养自己的艺术人才,在此创办了“中华艺术大学”。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在此举行。现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现代文艺团体。简称“左联”。1928至1929年间的革命文学论争,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提高了革命作家的思想理论水平。通过论争,各方的观点逐渐接近,提倡和发展普罗(英语proletariate音译“普罗利塔利亚”的简称,意为“无产阶级”)文学成为他们的共同要求,资产阶级文艺家对于革命文学的攻击,从另一个方面促使革命作家认识到必须联合起来才能有力地进行文艺思想斗争;苏联的“拉普”(全称“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日本的“纳普”(全称“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和“革命文学国际局”先后成立,也对中国革命作家的联合起了推动作用。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及其由于论争而暴露出来的弱点,引起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重视,加强了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帮助革命作家成立联合的团体。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于1930年3月2日在上海的中华艺术大学举行。到会的有冯乃超、华汉(阳翰笙)、龚冰庐、孟超、莞尔、邱韵铎、沈端先(夏衍)、潘汉年、周全平、洪灵菲、戴平万、钱杏邨(阿英)、鲁迅、画室(冯雪峰)、黄素、郑伯奇、田汉、蒋光慈、郁达夫、陶晶孙、李初梨、彭康、徐殷夫、朱镜我、柔石、林伯修(杜国庠)、王一榴、沈叶沉、冯宪章、许幸之等40余人。最初的盟员共50余人。大会通过了左联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选举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邨、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7人为常务委员,周全平、蒋光慈两人为候补委员。鲁迅在会上发表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说,强调革命作家一定要接触实际的社会斗争。他对左联工作提出四点意见:“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战线应该扩大”;“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左联一成立,立即遭到国民党政府的破坏和镇压,如取缔“左联”组织,通缉左联盟员,颁布各种法令条例,封闭书店,查禁刊物和书籍,检查稿件,拘捕刑讯,秘密杀戮革命文艺工作者等。人们习惯称为“左联五烈士”的李伟森(李求实,左翼文化工作者,不是左联成员)、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就是1931年2月7日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但左联仍顽强战斗,除上海总盟外,还先后建立了北平左联(又称北方左联)、东京分盟、天津支部,以及保定小组、广州小组、南京小组、武汉小组等地区组织。参加左联的成员,也不限于文化工作者,还扩大到教师、学生、职员、工人,盟员总数达数百人。 左联的领导机构,起初是常务委员会,后改称执行委员会(或两者同时并存),设秘书处,有行政书记负责日常工作。下设组织部、宣传部、编辑部、出版部、创作批评委员会、大众文艺委员会、国际联络委员会等。担任过左联领导工作的,除成立大会选出的常务委员之外,后来还有茅盾、冯雪峰、柔石、丁玲、胡风、以群、任白戈、夏征农、徐懋庸、何家槐、林淡秋等。左联内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党团”,先后担任党团书记的有潘汉年、冯乃超、冯雪峰、阳翰笙、丁玲、周扬等。在组织上,左联接受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的领导。 左联与国际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建立了联系,1930年11月,左联派萧三作为代表参加在苏联哈尔科夫召开的第二次国际革命作家代表会议。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加入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中国支部。 左联先后创办的机关刊物有《萌芽月刊》、《拓荒者》(二刊系接办)、《巴尔底山》、《世界文化》、《前哨》(第2期起改名为《文学导报》)、《北斗》、《十字街头》、《文学》、《文艺群众》、《文学月报》、《文学新地》等等;还秘密发行了《秘书处消息》和《文学生活》;并在《时事新报》副刊《青光》主办《每周文学》。另外有外围刊物《文艺新闻》。北平左联机关刊物有《文学杂志》、《文艺月报》等。东京分盟办有《东流》、《新诗歌》、《杂文》(后改名《质文》)。左联盟员以个人名义编辑的刊物有《无名文艺》(叶紫、陈企霞)、《文艺》(周文、刘丹)、《春光》(庄启东、陈君治)、《中华日报》副刊《动向》(聂绀弩)、《译文》(鲁迅,后为黄源)、《太白》(陈望道)、《新小说》(郑君平,即郑伯奇)等。左联领导的中国诗歌会有会刊《新诗歌》。 左联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自己的实践,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人都做了不少翻译介绍工作。左联从一开始就重视理论批评工作,其成员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对于“新月派”、“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自由人”、“第三种人”及“论语派”等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点,进行了批评。对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文艺政策,进行了批判和斗争。他们很重视文艺大众化的问题,先后在《大众文艺》、《拓荒者》、《文学导报》、《北斗》、《文学》、《文学月报》以及其他报刊上发表文章,展开热烈讨论,形成很有声势的文艺大众化运动。 左联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在创作方面取得巨大成就。革命作家在左联刊物和其他进步刊物上发表了大量作品,鲁迅的《故事新编》以及他和瞿秋白的杂文,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春蚕》,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丁玲、张天翼、叶紫等人的小说,田汉、洪深、夏衍等人的剧作,中国诗歌会诸诗人的诗歌,都以其思想上艺术上新的拓展,显示了左翼文艺的实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左联的培养下,涌现了沙汀、艾芜、叶紫、周文、蒋牧良、艾青、蒲风、聂绀弩、徐懋庸等一批文学新人。他们给文坛带来许多生气勃勃的作品,成为30年代文坛上活跃的力量。创作方面的巨大成就还在于出现了许多新的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题材和主题。革命者在白色恐怖下的英勇斗争,工人群众对资本家剥削的猛烈反抗成为许多作品描写的内容。农村生活和斗争的题材也进入了许多作家的创作视野,不少作品以真实生动的艺术画幅反映了农村贫困破产的景象,显示了广大农民的觉醒和斗争。此外,30年代动荡不安的城市生活也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真实、集中的反映。所有这些作品都体现着强烈而鲜明的时代色彩。 由于受到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左联在工作中有过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倾向。反映在创作中,不少作品内容上染有较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意识。有些作品还有公式化、概念化的弱点。对此,鲁迅曾进行过中肯而切实的批评。1936年春,为了适应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左联自行解散。 左联在国民党政府残酷压迫下顽强战斗了6个年头,粉碎了国民党当局的文化“围剿”,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军事上的反“围剿”斗争。左联培养了一支坚强的革命文艺大军,为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甚至建国以后的人民文艺事业准备了一批骨干人才。左联为建设人民大众的革命文艺作出了卓越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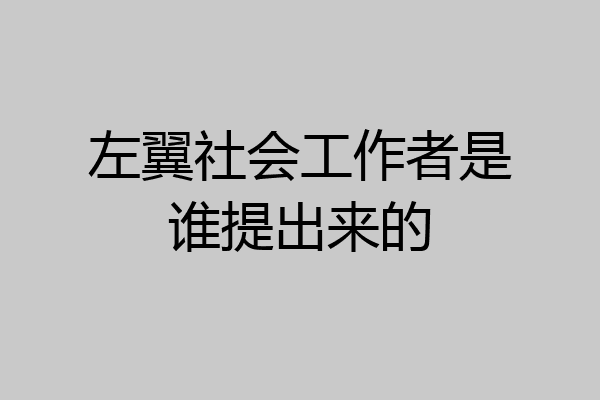

代号为喵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于1930年3月2日在上海的中华艺术大学举行。到会的有冯乃超、华汉(阳翰笙)、龚冰庐、孟超、莞尔、邱韵铎、沈端先(夏衍)、潘汉年、周全平、洪灵菲、戴平万、钱杏邨(阿英)、鲁迅、画室(冯雪峰)、黄素、郑伯奇、田汉、蒋光慈、郁达夫、陶晶孙、李初梨、彭康、徐殷夫、朱镜我、柔石、林伯修(杜国庠)、王一榴、沈叶沉、冯宪章、许幸之等40余人。最初的盟员共50余人。大会通过了左联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选举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邨、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7人为常务委员,周全平、蒋光慈两人为候补委员。鲁迅在会上发表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说,强调革命作家一定要接触实际的社会斗争。他对左联工作提出四点意见:“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战线应该扩大”;“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左联一成立,立即遭到国民党政府的破坏和镇压,如取缔“左联”组织,通缉左联盟员,颁布各种法令条例,封闭书店,查禁刊物和书籍,检查稿件,拘捕刑讯,秘密杀戮革命文艺工作者等。人们习惯称为“左联五烈士”的李伟森(李求实,左翼文化工作者,不是左联成员)、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就是1931年2月7日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但左联仍顽强战斗,除上海总盟外,还先后建立了北平左联(又称北方左联)、东京分盟、天津支部,以及保定小组、广州小组、南京小组、武汉小组等地区组织。参加左联的成员,也不限于文化工作者,还扩大到教师、学生、职员、工人,盟员总数达数百人。左联的领导机构,起初是常务委员会,后改称执行委员会(或两者同时并存),设秘书处,有行政书记负责日常工作。下设组织部、宣传部、编辑部、出版部、创作批评委员会、大众文艺委员会、国际联络委员会等。担任过左联领导工作的,除成立大会选出的常务委员之外,后来还有茅盾、冯雪峰、柔石、丁玲、胡风、以群、任白戈、夏征农、徐懋庸、何家槐、林淡秋等。左联内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党团”,先后担任党团书记的有潘汉年、冯乃超、冯雪峰、阳翰笙、丁玲、周扬、戴平万等。在组织上,左联接受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的领导。左联与国际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建立了联系,1930年11月,左联派萧三作为代表参加在苏联哈尔科夫召开的第二次国际革命作家代表会议。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加入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中国支部。左联先后创办的机关刊物有《萌芽月刊》、《拓荒者》(二刊系接办)、《巴尔底山》、《世界文化》、《前哨》(第2期起改名为《文学导报》)、《北斗》、《十字街头》、《文学》、《文艺群众》、《文学月报》、《文学新地》等等;还秘密发行了《秘书处消息》和《文学生活》;并在《时事新报》副刊《青光》主办《每周文学》。另外有外围刊物《文艺新闻》。北平左联机关刊物有《文学杂志》、《文艺月报》等。东京分盟办有《东流》、《新诗歌》、《杂文》(后改名《质文》)。左联盟员以个人名义编辑的刊物有《无名文艺》(叶紫、陈企霞)、《文艺》(周文、刘丹)、《春光》(庄启东、陈君治)、《中华日报》副刊《动向》(聂绀弩)、《译文》(鲁迅,后为黄源)、《太白》(陈望道)、《新小说》(郑君平,即郑伯奇)等。左联领导的中国诗歌会有会刊《新诗歌》。

健康是福83
左翼作家联盟,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 “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简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团体。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并先后在北平、天津等地及日本东京设立分会。领导成员有鲁迅、沈端先(夏衍)、冯雪峰、冯乃超、周起应(周扬)等。“左联”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文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曾有组织有计划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宣传和研究,批判各种错误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提倡革命文学创作,进行文艺大众化的探讨,培养了一批革命文艺工作者,促进了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它在国民党统治区内领导革命文学工作者和进步作家,对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在粉碎这种“围剿”中起了重大的作用。由于受到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左联”的一些领导人在工作中有过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对此,鲁迅曾进行过原则性的批评。1935年底,为了适应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左联”自行解散 1928年,创造社的主要成员,除郭沫若、成仿吾等外,又加入了新回国的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人。该社除出版《创造月刊》、《洪水》外,又出版了一种刊物《文化批判》。和创造社同时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还有太阳社。它的主要成员是蒋光慈、钱杏村、孟超等人。该社出版过《太阳月刊》、《海燕周刊》。《太阳月刊》停办后,又创办《新流月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下,在鲁迅、茅盾和创造社、太阳社的团结基础上,于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2月16日,鲁迅、瞿秋白等在上海成立“组织国内左翼作家联盟筹备委员会”。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召开成立大会。参加者有:鲁迅、茅盾、郁达夫(不久即退出)、周扬、沈端先(夏衍)、画室(冯雪峰)、钱杏邨、蒋光慈、冯乃超、田汉、李初梨、柔石等50余人。 “左联”在全国各重要地区建立了分部,展开了工作,先后主办的刊物有《萌芽》、《拓荒者》、《现代小说》、《北斗》、《前哨》、《大众文艺》、《文学月报》、《文艺新闻》《新文艺讲座》等。 在“左联”成立不到一年,青年共产党员作家柔石、殷夫、胡也频、李伟森、冯铿被敌人秘密枪杀。鲁迅说这些被害的同志是用他们的鲜血,写下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篇文章。“永远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不断的斗争”。 从1931年夏天起,瞿秋白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并和鲁迅成为亲密的战友。他们并肩战斗,对于“左联”成立后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起了巨大的作用。1936年初,为了适应抗日救亡的新形势,左联宣布自动解散。

YIFAN的新家
左派、右派 左派和右派,是相针对的两类政治派别的称呼,有时也分别称为左翼和右翼。由于历史与国家文化等,这两个名词并没有清晰和准确的定义,在不同地区和历史阶段的意义也不尽相同。 在现实中,多数人和政党的政治主张左右都有,很难清晰地划分一个人是左派还是右派。 来源 1789年6月,法国大革命的制宪会议上,教士和贵族大都坐在议会右边的席位上,资产阶级、城市平民、工人和农民则坐在左边。由此,“右派”或“右翼”成为保守派、反对社会变革的代名词,而“左派”或“左翼”则支持自由主义和革命,有时也指激进派。 此后,保守或变革成为划分左右的来源,但在实际中却非如此,一旦变革或激进的主张实现后,原来保守的主张反而要求改变现状,左右的称谓却依然保留下来,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后时期。政治观点的扩张性也与左右有关联,最早是由主张变革的左派提出许多扩张的政治诉求,但这些诉求在经历时间后,攻守之势完全反了过来。共产主义的主张最早是扩张性的,要求“推翻旧的世界与制度”,二战后欧美对共产主义的防范加强,在1950年代,美国国内开始了对共产主义的主动打压,其主张者被称为极右翼。 由于左右的这种模糊和变动性,同样主张的人群在不同国家和时期是相反的,常见的鹰派,在中国往往指左派,在日本则是右派。左派右派这样的术语是泛指概念,不会运用在研究具体政治主张、价值观、思想学派,一般用明确界定的宪政主义、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纳粹主义等。由于在特定的国家、区域,在特定的时期,左派与右派有明确的语境,所以它们依然是使用广泛的称谓。 由于左右的泛指性,根据其政治主张的程度,还被分成极左、中左、中、中右、极右等等,这些分类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和称谓。 西方的左右派划分标准 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非常动听,叫“自由、平等、博爱”。但任何激动人心的口号都有一个缺点,就是经不起推敲。自由与平等,看起来似乎并不相干,其实真正深刻的探询起来,发现两者之间根本就是矛盾的,每个人的天资、能力,背景,生存环境都是不同的,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发展,那么他们的财富、地位就不可能平等。如果要让每个人都在经济,地位,权力上“平等”,那么必然会限制强者的自由以保障弱者。 左右派起源于法国制宪会议,但很快定型成与初始含义毫不相干的两个集团。其中左派比较支持平等,强调建设福利国家,更多的通过国家干预手段帮助弱者,左派天生比较重视建立强势政府,右派比较强调自由,反对过高福利,比较支持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建立“弱”政府,反对对于强者的过多限制。但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只基于对平等与自由的偏重上。左派更偏重平等一点,右派更偏重自由一点。对基本限度的平等与自由权利,均持有同样的共识。 左派认为,政权、国家是人民的家长,政权迭换就和换个亲人一样不可思议。右派认为,国家、政府是人民的仆从,换个政权就和换个仆人没什么区别,觉得不好就应该换。其实左派右派都不同程度的反政府,因为左派认为政府的很多作为——比如外交方面——不让他们满意;右派则认为现行体制不能让他们满意。在这点上,两者间基本没有调和的可能。纠其原因,是因为左派比较相信集体的力量,认为强大的集体能给个人带来最大的公平和保障,右派则相信个人的力量,认为强大的个人能让集体更加自由和进步。 左派认为中国近代的衰落和现代的种种问题,都是外国势力侵略和干预造成的。右派则认为是中国衰落才引来外国侵略,建国后的困境则是由于我国政府的错误行为。“外因说”和“内因说”的争论,就和吃鸡蛋应该敲小头还是大头一样,属于比较无聊的争执,两派都是事后诸葛亮,两派都有理。 左派习惯将一切问题政治化,从文革时期四人帮反对周总理和邓副总理采购外国轮船,到现在万人签名抵制“新干线”一脉相传——绝对不能买仇人的东西。右派则认为经济利益优先,国家发展重要——凭什么花10块钱自己做,不买外面5块钱的?左派右派都宣称自己的观点最符合中国利益,至于到底哪派正确还是由时间去验证吧! 无论左派右派,谁也代表不了中国人民,因为老百姓全是中间派。某中间派说的好:“愤青百无聊赖,汉奸自作多情 什么是极左,什么是极右 所谓极左,就是把左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自由的底限”。为获得无差别的公正,而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为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必须建立一个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器,将人民的一切活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 所谓极右,如果把右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平等的底限”。把反对国家限制强者推演成要强者控制国家欺凌弱者,宣称“国家就是为强者存在的”(斯托雷平),实行寡头专政,取消对弱者的一切保护,一切自由。 为什么说极左制度是伪公平? 极左的目的是为获得经济上无差别的公正,但由于每个人能力、背景各不相同,要压制每个人的个性寻求公正,就必须实行极权。这样尽管每个人在经济上基本平等,但极权会造成权力的不平等。位高权重的,呼风唤雨,无所不为。地位卑贱的,连性命都无法保障。在权力倾轧中被淘汰下来的,往往境遇悲惨。这些大伙都很熟,我们曾经在这种制度下生存了很长时间。
优质社会工作者证问答知识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