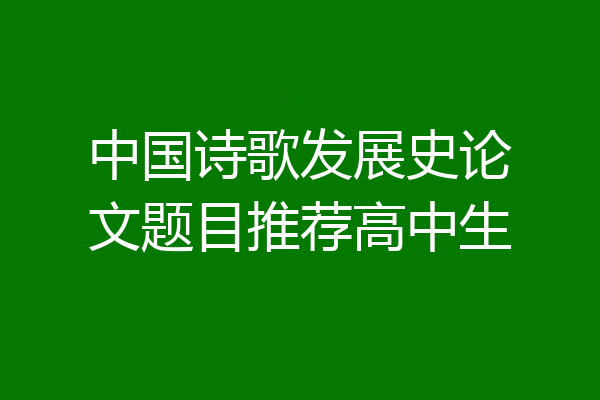fz35812
fz35812
中国的文学发展中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文学体裁的更变 总是呈跳变的趋势,也就是说文学的发展中并没有长时间的过 渡,也没有明显的标志。仿佛就是突然的从酝酿中挣脱出来, 马上就成熟了,就可以当作经典来用。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 就是宋词。我们知道词这种文学体裁是从外邦中传来的,起先 是些长短不一的曲子,后来由于文人的介入,而使它慢慢的从 纯粹的娱乐中解脱出来,变成高尚的,文学殿堂的重要支柱。 李白就写过两首著名的词。但是那时候诗还是占绝对的统治地 位的,这不仅表现在选材用士上,教坊中唱的也是诗 (王之涣 与王昌龄还曾经用这种方法来判断二人的优劣) ,可见这时的 词还是很微小的,几乎就没有别人在词上面下过工夫。这或许 也是因为那时的唐诗是无可比拟的。之后的几十年,词一直没 有大的进步。直到温庭筠的时代,忽然就有许多的词人出现了, 居然也就发展出婉约派这一巨大的词的团体,那么词的发展就 已经很完备了——从无到有,不过是几十年的时间,我们不能 不说它的发展是快的。而且象唐诗的兴盛是经过了南北朝乃至 于隋的发展才有的,那可以说是正常的,反之相比较宋词的诞 生与繁荣,就格外的仓促。但是词从诗之中脱颖而出是一场革 命,而诗从诗中的纯化只是沉淀,或许中国人的特点就是比较 勇于接受自己认为还可以而又没有冲突的东西,一旦讲到老祖 宗就英雄气短。 不仅仅是词这样,象起初的五言诗的出现,何尝不是从四言中 撕裂了脱出的呢,不过七言就没那么幸运。象上面所说的《诗 经》,不也是突变的么?而更为显著而有名,也更为意义远大 的例子就是屈原《离骚》的脱颖而出。那实在是中国文学的幸 运,因为从那以后,文学就从整体走向个人,个性融入了其中 ,而真正的个人创造的时代从此诞生了,从这之后,个人对于 文学的创造转入积极的态度,此后才真正的出现了百家争鸣的 局面。各种体裁的繁荣,形形色色文学流派的出现,都是《离 骚》将个性赋予诗歌后才产生的。 或许屈原才是第一个从战国的乱世中感受到痛苦的文人,更确 切的说是他是第一个这样的天才,所以他有那么多的郁积要诉 说,他从本身的要求出发,是想寻求宣泄的,诗歌对于他来说, 不再是赞颂的需要了,而是必须要倾诉的压迫。另一方面,他 在长年的放逐中接触了非常浓厚的民族文学的气氛,或许是出 于政治理想的沦丧吧,他并没有对于这些包含了优秀思想与内 容的东西视而不见,而是非常仔细的予以吸收,——有时候我 也奇怪为什么中国的官迷中居然跑出了这样一位讲求自然美的 士大夫来。但是这样的爱好使他的眼界大大的拓宽了,在很大 的意义上讲,这样的一位文人,才有创造的潜质,也从这时开 始,“国家不幸诗家幸”才成为普遍的事实。 我们说,屈原的诗歌不是出于赞颂的目的的,他是完全从个人 的角度,凭着个人的感受来写诗的,这与《诗经》是非常不相 合的,为什么呢,突然,由一个人的缘故,产生出这样的裂变, 并且影响了以后完全的诗歌界,或许我们应当承认这就是历史 发展的必要性。到了那个时代,应当是文体改变的时候了,继 续那种压迫式的创作方法,是不能带来新鲜的,充满创造力的 气氛的。我们说文学的发展,它的动力来自哪里,是我们天性 中就有文学的才能在内么?还是中国的古人就应该作文学的奴 隶?不是的,我认为我们对于文学的爱好与执着纯粹是由于愿 望的吸引,在古代又加上升官发财的直接经济利益的诱惑。可 以说人的一切行为从生物的角度来说都是本能的反映,文学也 是一种行为,那么它是那种本能的反映呢?这是人的一种宣泄 的要求,是我们不甘于冷清的寂寞所发出的一种呼喊,在这些 以外,还有创作的要求,我们对于客观事物的直接认识以及思 索的结果,使我们有记录的必要,从感情的角度来说,就是文 学,倘若一定要说文学是美的再现,是神性在人的躯体中的反 射,我也赞成,因为不管怎么说,文学所表现的,还是倾向于 好的一方面,主题是赞美与劝恶。所以有人说文学的主题是美, 这也对。但是对于起初的古人,文学就不仅仅是美了,也不是 那永恒的真,文学所体现的,是一个人赤裸裸的自我,是对于 一层层压迫的不可理解,是呼喊。文学是工具,正如同人类刚 刚起步的时候的石刀石斧一样,他们凭借这样的工具,在历史 的道路上艰难的前进着,居然还创造出那么辉煌的成果,真是 不简单。 反过来看屈原,他是尤其艰苦,因为他没有效仿的对象,他的 一切都是从头开始;但也可以说他是幸福的,因为他也没有过 多的束缚,他所要做的就是他所想的,完全不用有什么后顾之 忧,在这一点上,他又有其开创的资本。 屈原不但将个性引入了诗歌或者说是文学中,而且他拓宽了文 学的境界,他从民间文学中吸纳而创作的《九章》以及《离骚》 是很经典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将诗的凝练与先秦散文的 优秀的表达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独特的体裁,这种体裁或 者就是汉赋的前身,因为它们的承接关系实在是太明显了,这 就是一个时代的开始。另外的关于他在内容和表达上的特点, 就不用再多说了,那已经是路人皆知的了。 这样的说来,屈原在文学上的贡献就是: 1.个性的引入。 2.体裁的拓宽。 3.对于民间文学的有意识的吸收。 4.表达上的不拘一格。 之后的时代,就是汉赋的了。那是又一个了不起的辉煌,文学 到了此时又应该循序渐进的发展了,但是它又没有,它的后来 是又一个革命性的突变,就是由四言到五言的跳入,由散体到 规格范化的跃变。这一突变,才使以后的诗词的发展有了广阔 的天地,也奠定了唐诗宋词傲视天下的先天基础。 -- 或有体制未属,音律不谐;人或为笑,己亦自怯。 同读君子,谅哉谅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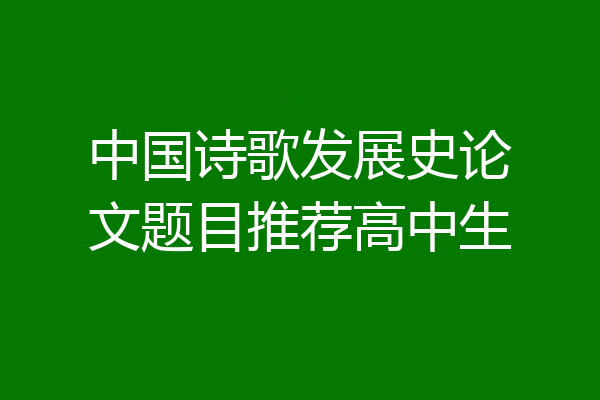
汉代,出现了为配合音乐而歌唱的诗即“乐府诗”。在语言上有四言,五言,杂言,但多数是五言的。这以后曹操父子以及陶渊明为首的文人们发展了五言诗。同时,七言诗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乐府诗的代表作<<孔雀东南飞>>,<<陌上桑>>在诗歌历史上有很大的文学价值。 汉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型时期。汉(末)魏六朝在政治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和黑暗时期,但在思想文化艺术史上却非常重要,其影响之深远,直达现今。 在魏晋南北朝以前,诗的格律和声韵还没有形成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律,只是由作者按照个人的内容需要和声韵感觉来进行写作。到了魏晋,由于受到了印度(古称天竺)的梵音学的影响,我国的声韵学得到了发展。齐梁的周喁和沈约总结了汉字的发音规律,提出了“四声”“八病”之说,使诗歌创作由自然的声律发展到讲究追求声律,出现了作诗要注意平仄和韵律的性质,形成了格律诗的主要内容。 说起汉魏诗学,我们不得不提起建安文学。建安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是三曹父子兄弟以及孔融、王粲、刘桢、阮瑀、徐干、陈琳、应暘等。这些人被称为“建安七子”。后人称这一时期是“结束汉响,振发魏音”,它标志着汉代文学风格样式的结束,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唐代李白有诗赞扬“蓬莱文章建安骨。中国自孔子以后相当一个时期里,文学崇尚理性,以说理,叙事为主,所以有“诗言志”、“文以载道”的说法,成为传统。但三国时期却出现了“缘情”的主张,与“言志”并提。“缘情”大体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抒情。象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曹丕的“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等等,就是这样的诗歌。 汉魏诗学除了建安诗体外,还有一继承了《诗 国风》“民间自然性情之响”的诗歌体裁,即“汉魏乐府”。继《诗经》《楚辞》之后,两汉乐府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的景观,作为一种新的诗体,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汉乐府以其匠心独运的立题命意,高超熟练的叙事技巧,以及灵活多样的体制,成为中国古代诗歌新的范本。例如格调自由,情感真切的《古歌》;坦露女子对爱情的忠贞誓言的《上邪》;形式齐整,言词优美隽永的《迢迢牵牛星》;以及故事曲折起伏,人物性格鲜明,言语明快简洁的叙事类民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 受汉乐府的影响,汉魏诗学经历了由叙事向抒情,又模仿民歌到作家独创的转折。列如传承至今的《古诗十九首》即是出自汉代文人之手。而建安文学的创作,则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徒诗的转变。中国传统诗歌也由此迈入雅文学的行列。 此外,诗歌从四字一句的“四言诗”发展到今天仍然很通行的五字或七字一句的“五言”、“七言”诗体,也是在汉魏之际确立的。一般认为,曹操的《观沧海》、《龟虽寿》等四言诗是前代诗歌的“压卷之作”,也就是说四言诗中最后出现,却又是最好的作品,而曹丕《燕歌行》的灵活自由的七言诗,则为后来的七言律诗开创了一个新时期。 魏晋时期,其诗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魏晋风度”。它包含有“狂饮”、“放诞”等狂放的行为,有“清谈”、“隐逸”、“拟古”一类奇特的风气,也有儒、道、佛混杂的思想。在题材上,汉魏六朝的诗歌除了“缘情”之外,又产生了“山水”、“田园”和“玄言”等不同诗派;在诗风上,则出现了自然清新,明白晓畅的主流;在形式上,则共同趋于五七言的整齐,进而形成了完整严密的格律。 三、盛唐诗风 如果把中国诗歌流变的历史,譬作九曲黄河,那么究其源始,犹如雪水消融,点点滴滴,接下来则如轻溪泻地,随意流转,灵动自如,终于在汉魏六朝间进入了一个汇湾,吸纳他源,积蓄能量,汗漫浩荡。直至隋唐则突然变化为飞瀑万卷,声势浩大,奔腾不息,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对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怎么估价都不算过分的。鲁迅答杨霁云函锐:“我认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作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甘而不必动手。”(《鲁迅书信集》 唐朝是我国诗歌的黄金时代,约300年中,流传下来的诗歌就将近5万首,比西周到南北朝的1600多年留下的诗篇多出2倍多。唐诗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以大诗人李白、杜甫的诗歌成就最高,达到诗歌创作的高峰。令后世诗人豪士可望而不可及。这是中国诗歌的宝藏,也是中国诗歌的丰碑! 陈子昂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骨与兴寄两大主张。陈子昂的诗歌鲜明的表现了他的理论,无论是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都是如此。形式上都是五言古诗,内容表现是多方面,十分丰富的。 陈子昂所追求的是风骨,与他大致同时的张若虚,却在创作中追求明丽纯美。他的一首《春江花月夜》达到了纯美的极至。闻一多在《宫体诗的自赎》中总结《春江花月夜》说:“向前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因此,向后也就和另一个顶峰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 盛唐之后,国力由盛而衰,而诗歌的格调也身受其影响。如冷落寂寞的大历诗风。此后,诗人们着力于创新,创作出大量极富新意的各体诗歌。尤以韩孟诗派为盛,其代表人物有“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古今之穷”的韩愈等。韩愈致力于诗歌创新,主张“不平则鸣”。陈寅格先生称其诗“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 与韩孟诗派同时稍后,中唐诗坛又崛起了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这派诗人重写实、尚通俗。二者虽背道而驰,但实质却都是创新,取途虽殊而归趋则同。 步入晚唐,社会衰败,政治黑暗。诗坛又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诗人。如杜牧,贾岛,隐士诗等。而晚唐诗歌的集大成者乃属李商隐。李诗艳而不靡、凄美浑融、情调幽美、意象朦胧,最为杰出的则是其以无题为中心的爱情诗。 唐诗是唐人的是一种生存和竞争方式,也是唐人的一种思维方式。他们状物言情,或者表达曲折微妙的情绪,索性直接以诗为言,信手拈来。研究唐诗兴盛之由的著作如林,但除了从经济政治立说的“反映论”外,我们似更应该注意文化的因由。我们谈“唐诗”,不应该离开“唐风”。 四、诗的低谷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是经历了盛唐之后宋元明清的诗歌的最贴切的写照。随着诗歌在唐代达到鼎盛之后,诗歌在文坛中的地位逐渐衰落,本来桀傲不驯的诗歌洪流,在此之后一变而为一副循规蹈矩,安详驯顺的模样了。 经历了隋唐盛世,封建社会在浩瀚的中国历史中逐渐发展到了顶峰。
诗歌在中国源远流长,绵延数千年,取得了光辉灿烂的成就。早在西周至春秋时代,我国诗歌就已产生了大批辉煌篇章,其标志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诗经》收诗305篇,分“风”、“雅”、“颂”3部分,都是可以配乐演唱的。《诗经》的篇章大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人民性,善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句式以四言为主,多用重章叠句,为后世文学创作奠定了深厚的人文基础和艺术底蕴。战国后期,在南方的楚国产生了一种具有楚文化独特风采的新诗体——楚辞(骚体)。楚辞句式长短参差,以六言、七言为主,多用“兮”字。楚辞的奠基人和主要作者屈原,运用这种形式创作了《离骚》、《九歌》、《九章》等不朽诗篇,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其代表作《离骚》,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为宏伟瑰丽的长篇抒情诗。屈原之后有宋玉、唐勒、景差等楚辞作家。楚辞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从民间集体歌唱发展到诗人独立创作的更高阶段。《诗经》和楚辞,是后世诗歌发展的两大源头,在文学史上并称“风骚”,共同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并驾齐驱、融会发展的优秀传统,并垂范于后世。汉代前期,文人诗坛相对寂寥,民间乐府颇为活跃。“乐府”原指国家音乐机构,后代将乐府所收集与编辑的可以配乐演唱的歌辞也称为“乐府”。汉乐府民歌是汉乐府的精华。汉乐府民歌继承《诗经》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传统,多“感于哀乐,缘事而发”,通俗易懂,长于叙事,富有生活气息,句式以杂言和五言为主,体现了诗歌艺术的新发展。《陌上桑》与《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民歌中最优秀的作品,也是叙事诗的代表作。《孔雀东南飞》是我国诗歌史上第一篇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的长篇叙事诗,凡353句,1 765字,被称为“长诗之圣”、“古今第一首长诗”。在汉乐府的影响下,文人五言诗逐渐发展成熟,其标志是东汉末年出现的《古诗十九首》。这是—组由寒门文人创作的抒情短诗,情调感伤,言短情长,委婉含蓄,质朴精练,被誉为“一字千金”、“实五言之冠冕”。汉末魏晋时期,文学进入自觉时代。建安时代,“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文人诗歌却呈现了“五言腾踊”的大发展局面,以“三曹”父子和王粲等“建安七子”为中心组成邺下文人集团。他们的诗作大多反映时代动乱和人民疾苦,抒写个人理想抱负,具有“慷慨以任气”、“志深而笔长”的风格,此即后世称道的“建安风骨”。建安诗歌以曹植和王粲的成就最为杰出。魏晋之交,世风变易,“竹林七贤”是正始时期的代表诗人群体,其中阮籍、嵇康名声最著,成就最高。阮籍的82首《咏怀诗》是我国第一部规模较大、内容丰富的个人抒情五言组诗,嵇康则开拓了四言诗的新境界。西晋太康年间,诗坛上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称。陆机、张协、潘岳等人的作品追求丽辞缛采,开中国诗歌雕琢堆砌的流风;左思则独树一帜,继承建安文学传统,其《咏史》8首借咏史来抒怀,情调高亢,笔力矫健,有“左思风力”之称。东晋玄言诗泛滥一时,直到东晋末年陶渊明的出现,才使诗坛骤添异彩。陶诗多写田园生活,风格自然冲淡,“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轼语),对唐代山水田园诗派有直接影响。南北朝时期,南方的代表诗人有谢灵运、谢、鲍照等。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实现了玄言诗向山水诗的转变。谢受其影响,正于描写山水,与谢灵运合称为“大小谢”。鲍照擅用七言古体抒发愤世嫉俗之情,风格俊逸豪放,为唐代七言歌行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北方最有成就的诗人是由南入北的庾信,他以刚健之笔写乡关之思,融合南北诗风,成为六朝诗歌的集大成者。南北朝乐府民歌足与汉乐府前后辉映。南朝民歌清丽婉转,代表作是《西洲曲》;北朝民歌粗犷刚健,代表作是《木兰诗》。唐代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诗体完备,流派各异,名家辈出,成就卓著。“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和稍后的陈子昂,上承汉魏风骨,力扫齐梁宫体颓靡诗风,发出清新健康的歌唱,为唐诗的发展铺平了道路。盛唐时期首先出现两大诗歌流派:一是以王维、孟浩然等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多摩山范水,抒写闲情逸致,风格清新自然;二是以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为代表的边塞诗派,多写边塞风光和军旅生活,或慷慨悲壮,或雄奇瑰丽。接着李白、杜甫横空出世,被称为我国诗歌史上雄视古今的“双子星座”。“诗仙”李白继承和发扬中国诗歌的浪漫主义传统,歌颂祖国大好河山,表现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感情奔放炽烈,风格豪放飘逸。“诗圣”杜甫继承和发扬传统的现实主义精神,其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风貌,被誉为“诗史”,感情内在深沉,风格沉郁顿挫。李、杜分别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极高的成就而成为泽被百代、彪炳千秋的伟大诗人。安史之乱后,进人中唐时期,经过短期的过渡,唐诗呈现第二次繁荣。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倡导了一场新乐府运动。他们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创作了《新乐府》、《秦中吟》等针砭时弊的讽喻诗